[樂游網導讀]剛剛LOL官方放出了蝕魂夜的傳說第二章內容,不知道大家都看過沒有,這次小說內容講述了一段什么樣的神器故事呢,一起來看看吧。
剛剛LOL官方放出了蝕魂夜的傳說第二章內容,不知道大家都看過沒有,這次小說內容講述了一段什么樣的神器故事呢,一起來看看吧。

厄運小姐合上手槍的彈倉,將它們并排放在桌上的短劍旁。狂亂的鐘聲和尖嘯的警報聲回蕩在山下的城市里。她很清楚那代表著什么。
蝕魂夜。
厄運小姐根本沒把即將到來的風暴放在眼里。這座她剛剛占據的山頂別墅所有的窗戶都敞開著,挑釁著死亡的陰影。嗚咽的海風帶著惡鬼的饑渴和刺骨的寒冷撲面而來。
這座別墅坐落于比爾吉沃特東邊的一處懸崖上,原本屬于一個惡貫滿盈的黑幫頭子。在普朗克倒臺的混亂中,他被人拖出被窩,砸死在大理石階上。
別墅現在的主人就是厄運小姐。她絕對不會允許同樣的事情再發生一次。她抬起手,撫摸著俄洛伊在拜恩的葬禮上送她的掛飾。珊瑚的觸感帶著溫熱,雖然她并不真心相信它所代表的意義,但這無疑是一件漂亮的小玩意。
房門悄聲打開,她也放開了手里的掛飾。
她沒有回頭便知道來人是誰。只有一個人敢不敲門就進屋。
“你在干什么?”雷文問。
“你覺得我在干什么?”
“我覺得你在干蠢事,非常蠢。”
“蠢事?”厄運小姐雙手放在桌面上,“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,才干掉了普朗克。我絕對不會讓蝕魂夜就這樣——”
“就哪樣?”
“把這塊地方從我的手里奪走。”她猛地抓起手槍,插進了后腰的皮套里。“你也不能阻止我。”
“我們不是來阻止你的。”
厄運小姐一回頭,看見雷文站在門檻那里,身后是一群她最精干的手下。他們全副武裝地在門廳里等待著,手里拿著滑膛槍、左輪手槍、鏗鏘作響的土制破片炸彈和彎刀。武器品種繁多,就像是剛剛洗劫了一座博物館。
“看起來,你要干的事情也聰明不了多少。”
“是。”雷文走向敞開的窗戶,將百葉窗簾拉下來。“你覺得我們會讓自己的船長獨自面對嗎?”
“為了殺掉普朗克,我自己也差點兒沒命,而且這事還沒結束。我不指望你們跟著我去,至少今晚不行。”厄運小姐走到手下面前站定,雙手歇在核桃木的手槍柄上。“這場戰斗與你們無關。”
“鬼扯,當然有關。”雷文說。
厄運小姐深吸一口氣,點了點頭。
“有十成的可能性,我們看不到早晨的太陽。”她的唇邊不禁鼓起一絲笑意。
“船長,這也不是我們第一次經歷蝕魂夜了。”雷文拍打著劍柄頂端的骷髏頭,說道:“這也絕對不會是最后一次。”
II
冬吻號剛出現在視野里,奧拉夫就聽到了尖叫聲。
他一開始沒太在意,因為比爾吉沃特成天有人尖叫。但當他看到男男女女恐懼地從船塢邊逃開時,他的好奇心被撩起來了。
人們慌里慌張地從各自的船里逃到岸上,鉆進曲里拐彎的街巷拼命逃跑。他們頭也不回地逃命,有個倒霉的船員被絆進了水里也沒人理睬。
奧拉夫見過不少人在戰場上逃命的樣子,但這次有些不同。他感覺到一種更純粹的恐懼。非要形容的話,那些在冰巫盤踞的冰川下凍僵的尸體臉上的表情更加類似。
碼頭周圍關窗戶的聲音連成了一串。奧拉夫看到各家門前掛著的那個古怪標志,每個都撲上了厚厚的白色粉末。懸崖高處的巨型絞車正向上吊起由船艙改造成的木材預制件。
他在認出了一個酒吧老板。那個小破酒屋賣的啤酒淡得跟巨魔的尿差不多。奧拉夫朝老板揮手。
“這是怎么回事?”
酒吧老板搖搖頭,指指海面,然后砰地關上了門。奧拉夫把海魁蟲的牙齒放在石頭地面上,轉向海面想看個究竟。
起初他以為是一場正在路上的風暴,但再仔細看卻發現,那不過是厚重的黑色海霧而已。只是這霧氣移動的速度非比尋常,而且流動的感覺異常奇怪。
“啊,終于,”他取下勾在皮帶上的斧頭,“機會又來了。”
他把斧頭在長滿老繭的兩手間換來換去。斧柄上裹著的皮革飽經戰陣,摸上去令人心安。他開始活動肩膀的肌肉。
黑霧卷上了最遠處的幾艘船,奧拉夫的雙眼猛然瞪大了。無數亡靈,仿佛來自最黑暗的噩夢,正在黑霧之中翻滾。一名身材高大的恐懼騎士,胯下是一匹奇美拉[注 :希臘神話中獅頭、羊身、蛇尾的噴火怪獸。]一樣龐大的戰馬。他身前橫架著一把黑色的巨鐮,蒼綠色的火焰環繞著刀鋒。亡靈們離開他的身邊,急速地朝著比爾吉沃特的碼頭推進。
奧拉夫曾在當地人悄聲的低語中聽到過一個詞匯,蝕魂夜。好像是一個跟毀滅與黑暗有關的時節。但他沒想到自己的運氣這么好,撞上的時候恰巧手里還握著斧頭。
死亡的主宰露出了它的爪牙,一頭撞進成群的船只中,輕易地撕碎了一切。船帆和纜繩就像腐爛的肉片一樣化為碎屑。船身被拋離水面,然后砸在另一艘船上,連沉重的桅桿也碎成了木片。
一個幽魂飛進了冬吻號的船身,然后,奧拉夫就眼睜睜地看著龍骨穿出船體,斷成了幾截。只一下心跳的瞬間,整艘船就凍成了一坨木板,然后就像裝滿了石頭一樣沉下去。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落進水中,有某些東西伸出枯槁的肢體和掛著魚鉤的嘴巴,將弗雷爾卓德的水手們拖進了海底。
“奧拉夫會讓你生不如死!”他狂怒地大叫著,沿著碼頭沖刺起來。
翻滾的海面上升起許多亡靈,冰冷的爪子紛紛劈向奧拉夫。他的斧頭劃出一道閃光的弧線,發出破空的聲響,斬向領頭的亡靈。耳邊響起尖銳的嘯叫,亡靈們自覺地避讓著斧刃。臻冰加持過的利斧可比任何魔法都更加致命。
但好些亡靈沒能從他的斧頭下幸免,它們號哭著再次死去。而奧拉夫開始唱起歌來。這是他為自己光榮戰死的時刻提前譜寫的歌謠。歌詞雖然簡單,但其中的氣勢卻和漫步冰原的吟游詩人們筆下的傳奇相差無幾。他究竟等了多久,才能放聲唱出這些詞藻?又有多少次,他曾害怕過自己根本沒有機會唱起這首歌?
一陣發光的霧氣一下子籠住了他,霧中的鬼怪們如饑似渴地圍在他周圍。他的霜鱗甲上結了一層薄冰,亡靈致命的觸摸讓他感覺如同灼燒一樣的疼痛。
但奧拉夫的雄心卻不甘屈服。狂戰士的意志非他人所能理解,他的血液因狂怒而沸騰起來。他抖擻身體,撇開幽魂帶來的疼痛。他感覺自己正在逐漸失去理智,只任憑怒意不斷地堆積。
他咬破嘴里的肌肉,嘴角隨即泛起了猩紅的口沫。他怒吼著,像瘋子一樣揮舞著斧頭。他完全感受不到半點疼痛,一心只想著把敵人盡數砍死。
哪怕它們已經死過一次了也無所謂。
奧拉夫收回斧頭,蓄力后剛要揮出,卻聽到身后傳來圍欄和房梁倒塌的巨響。激起的碎木和石子像瀑布一樣撲面而來。他轉身尋找新來的敵人,任由鋒利的碎塊劃破他的臉頰,和拳頭大小的石塊砸在他的手臂上。伴隨著動物的體液和急雨一般落地的聲響,黑霧中傳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。
他看清了那是什么。
屠宰碼頭的殘跡中,海魁蟲的亡靈昂首而立。它身如巨輪,怒不可遏,鬼氣森森的觸手高舉到半空,然后猛地砸在地上,發出雷公降世一般的聲響。整條街轉眼便化作一攤廢墟。而奧拉夫意識到他終于找到了完美的對手,以符合他對死亡的期待。狂戰士的怒意再次暴漲起來。
他舉起斧頭,向對手致意。
“來吧美人兒!”他一聲高喊,沖向了自己的末日。
III
女人很漂亮。一對杏仁似的大眼,飽滿的嘴唇,還有德瑪西亞人典型的高顴骨。這幅肖像算得上是杰作,但它卻沒能體現出賽娜的力量和決心。
他很少會打開這個掛盒,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心要是沉溺于悲傷之中,只會讓他變得軟弱。悲傷就是鎧甲上的破綻。盧錫安無法容忍自己徹底地沉浸在失去她的悲痛中,所以他果斷地合上了掛墜。他明白自己應該將這串項鏈埋在這個山洞的沙土中,但他卻無法把有關她的回憶像她的尸身那樣葬在黃土之下。
他必須隔絕悲痛,直到殺死錘石為賽娜報仇那天為止。
只有到那時,盧錫安才會放肆地為她痛哭,并向面紗之女[注:德瑪西亞人所敬奉的死神。在其他地方,人們稱她為羊靈。獻上供品。
那個可怕的夜晚已經過去多久了呢?
他感到悲傷如同無底的深淵,窺伺著將他徹底吞沒的機會。然而,他又一次硬生生地壓住了自己的情緒。他回憶起從教團那里學到的本領,開始默念一段咒文。他和賽娜都知道這段咒文,目的在于把任何情感都關在門外。唯有這樣,他才能進入平衡的境界,才能面對超出想象的恐怖。
悲傷慢慢退了下去,但終究沒有完全消散。
只有在他感覺自己與賽娜的回憶漸行漸遠的時候,才會勉強自己打開掛盒。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想起很多細節,包括她下巴的弧線、皮膚的觸感、還有確切的瞳色。
復仇的路走得越久,也就離她越遠。
盧錫安抬起頭從肺中呼出一口氣,強迫自己的心跳放慢下來。
洞穴的四壁是暗淡的石灰石構成的,所在的懸崖上方就是比爾吉沃特。在水流的運動和當地居民的采石工程雙重作用之下,城市下方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迷宮。沒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。蒼白的墻上蝕刻著回環的螺線、涌動的潮水以及一些像是不會眨動的眼睛的圖案。
他知道這些符號都來自當地的宗教,但刻下它們的人已經很多年沒有來過這里了。而他是跟著自己教團的密符才找到這里的。在瓦羅蘭大陸上的任何一個城市,密符都標示著避難所和支援所在的位置。
洞穴中只有洞頂反射的點滴微光,但當他的眼神隨著螺紋刻線移動時,他的手心開始微微發亮。
讓我作你的盾。
盧錫安低頭看去,賽娜的話語清晰得仿佛她就在身旁。
項鏈掛盒正閃耀著搖曳的綠色火光。
他將項鏈掛回脖子上,然后拔出了那對曾是遺物的雙槍。
“錘石……”他的聲音仿佛囈語。
IV
比爾吉沃特的街道已經幾近廢棄。海上的鐘聲依舊兀自響著,充滿恐懼的哭號在山下回蕩。整個鼠鎮已完全浸在了黑霧中,哀悼塢的廢墟上狂風呼嘯。火焰沿著屠夫之橋一路焚燒,一團透著微光的霧霾在灰港上方的懸崖處盤桓。
上城區的人們躲在自己家中,向胡子女士祈禱著蝕魂夜饒過他們的性命。而那些屋不蔽體的窮苦人就沒那么幸運了。
每個窗戶前都點著鯨糞制成的守夜燭,火光透過海玻璃的瓶子瑩瑩跳動。家家戶戶的門板上都掛著點燃的女王草,窗欞用長條木板釘得死死的。
“人們真的相信女王草有用?”厄運小姐問。
雷文聳聳肩。他的嘴唇抿成一條細線,聚精會神地搜索著霧氣中的危險,眼眶周圍的皺紋都繃緊了。
他從衣服底下抽出一根悶燃著的草根。
“信則有,不是么?
厄運小姐拔出雙槍。
“我信這個,還有你們。你還帶了別的武器嗎?”
“這把彎刀,保護我安然度過了六次蝕魂夜。”他敲著劍柄說。“我向胡子女士獻了一整瓶十年陳釀的朗姆酒,然后我就買到了這把刀。賣刀的人發誓說,刀鋒用的是質地最純的炎陽鋼。”
厄運小姐只看了一眼他的刀鞘,就知道雷文當時被人騙了。護手部分的做工實在過于簡陋,不可能出自德瑪西亞工匠之手。但她并不打算告訴他。
“你呢?”雷文問。
厄運小姐輕拍了一下子彈袋。
“你們每個人都是在麥龍黑酒里泡大的。”她提高聲音,好讓三十來個人都能聽到。“如果死靈想干一架的話,就讓它們見識一下什么叫烈性子!”
壓抑的陰云之下,沒人笑出聲來。但她確實看到幾個人的臉上浮出了笑意。對于這樣一個夜晚來說,那就足夠了。
她轉身往山下的比爾吉沃特走去。走下懸崖上嵌入石壁的曲折樓梯,經過爛麻繩捆扎的隱秘小橋,穿過多年無人涉足的羊腸小道,一路向下。
她帶著手下鉆出一條小路,來到一塊由棚屋屋頂組成的開闊地帶。棚屋漂在水中,成群地擠在一起,屋檐交錯,似乎在互相低語。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雜亂的漂木,上面的霜結成細密的紋路。冰凍的風穿過錯雜的廢墟,帶來遠處的啜泣和慘呼聲。殘存的建筑之間架著桅木,上面掛著火盆,里面燜著一些奇怪的藥草,正散出縷縷青煙。水潭中倒映著一些詭異的影子,粼粼波動。
這里往日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市場。人們在相接的船舷處搭起了各色小攤。肉商、酒販子、海盜、賞金獵人和乖戾的流浪漢從世界各地涌到這里。在比爾吉沃特城里幾乎任何地方都能清楚地看到這里,而這正是厄運小姐所希望的。
霧氣開始在木頭上凝集。
廢棄的船首像臉上流下了凍結的淚珠。
霧氣和暗影匯聚起來。
“扒手廣場?”雷文說。“怎么會走到這里?我以前在這兒混過的。我還以為我已經知道所有進出的路了。”
“并不是所有。”厄運小姐說。
街道兩旁的房屋在黑暗中一片死寂,破爛的帆布窗簾正翻飛著。她努力不去看窗簾后面的圓窗里有什么東西。
“為什么你會知道這些路?我居然都不知道。”
“比爾吉沃特跟我天生一對,所以她會告訴我很多秘密。這些暗巷黑街的位置,你永遠也不會知道。”
雷文咕噥一聲,帶著眾人分散開來。
“然后呢?”
“等。”厄運小姐看著他們走到廣場中心,毫無遮掩地暴露在空地上。
黑霧的深處有東西在翻滾,帶得霧氣痙攣似地抖動。
一個鬼火形態的骷髏頭從黑暗中探出來,眼窩空空,尖牙利齒。它的下顎拉開到任何關節都無法做到的地步,喉嚨里刺出一聲哀慟的嘶叫。
厄運小姐的子彈傾瀉而出,全部鉆進了骷髏的眼眶。只聽得一聲不甘的利叫,骷髏便散去了形體。她甩開手槍彈倉,極其利落地又裝滿了子彈。
突然一瞬間,一切死寂。
黑霧猛地炸開,無數亡靈尖叫著涌進了廣場。
V
奧拉夫砍開海魁蟲的身體,又一次鉆了出來。
他像個失心瘋的木匠,興高采烈地揮著斧子左砍右劈,完全不計后果。雖然怪物的肢體如同霧氣般有形無實,但在他刮著冰風的斧刃招呼下,也如血肉一樣皮開肉綻。
幾條觸手高高揚起,繼而猛然拍下,卻撲了個空。奧拉夫雖然壯實,但速度卻毫不遜色。手腳不利索的戰士在弗雷爾卓德可沒法活下來。他就地一滾,反手劈出,一條觸手被齊根斬斷落在地上,然后消散無蹤。
他的身上披著鮮血,仿佛一件艷紅的壽衣。四周舞動的觸手不停向他抽過來。一片混亂的景象里,他看見了海魁蟲的腦袋。
它的眼睛里跳動著憤怒的靈火。時間似乎停滯了一瞬,他們之間的某種聯系被喚醒了。
這怪獸的靈魂認得他。
奧拉夫快樂地大笑。
“你見到干掉你的人了!聯結我們的正是死亡!要是你殺了我,我們就可以在另一個世界永遠戰斗下去了!”奧拉夫大吼。
面對這樣的強敵,永世相爭的渴望為奧拉夫酸痛的肌肉又注入了力量。他奔向怪獸大張的嘴,不顧海魁蟲的觸手甩在他身上的劇痛——這比洛克法海岸的凜風更甚百倍。
他高高地躍起,斧頭舉過頭頂。
他的眼前便是光榮的死亡。
一條觸手凌空纏住他的大腿。
奧拉夫被觸手一甩,劃出一道令人眩暈的弧線,拋到了半空中。
“來吧!”奧拉夫聲如炸雷,利斧朝天,向他和他的敵人共同的命運致敬。“至死方休!”
VI
一個幽魂伸著爪子,滿口冰冷的尖牙,從滾滾涌動的亡靈中沖出來。厄運小姐一顆子彈正中它面門。幽魂化作一陣煙塵,被風吹散了。
又一槍過去,另一個亡靈也退散無蹤。
她雖然心里也有些害怕,但卻微微一笑,然后飛快地竄到一根系纜樁后面換子彈。石頭樁子歷經風雨侵蝕,上面刻著河流之主的雕像。不知哪來的沖動,她傾過身子,在他咧嘴大笑的臉上印下一個吻。
信則有。
那該信神,還是子彈?亦或是,她自己的本事呢?
手槍咯噔一響卡住了,她臉上的笑意登時退去。母親的告誡從記憶最深處浮現出來。
“莎拉,如果讓別人來配火藥,你的槍就會這樣。”厄運小姐喃喃地說。她把手槍插回皮套,抽出了自己的佩劍。這是她從一個當時正北上前往恕瑞瑪的船長手里搶來的戰利品。做工精湛,堪稱制劍工藝的典范。
厄運小姐翻身站起,手槍快速擊發,同時揮劍砍向霧中的靈體。槍火摧枯拉朽,劍光矯健如電。這些亡靈會感受到肉體的疼痛嗎?似乎不太可能,但她確實打到了什么東西。
她無暇考慮太多,而只感覺無論那是何方神圣,都會在她的劍下被打回原形。
呼嘯的亡靈風暴吞沒了扒手廣場。它們張揚著爪子,追捕著逃命的人群。有些人的血液被凍成了冰棍,有些人則眼看著自己的心臟被扯出胸腔。死了七個人,他們的靈魂從尸體上被剝離出來,變成了亡靈中的一員。但她英勇的部下毫不退縮,他們舉起火槍和長劍殊死搏斗,嘴里要么喊著胡子女士、要么是自己的愛人,或者干脆是某些遙遠地方的異教邪神。
信就行了。厄運小姐心想。
雷文一只腿半跪在地上,臉如金紙,呼吸急促得就像是在碼頭上干了一整天。幾縷霧氣像蛛絲一樣黏上了他,脖子上那根陰燃著的女王草發出劇烈的桃紅色光芒。
“站起來!還沒打完呢!”她沖著雷文大喊。
“不用你跟我說!”他咬著牙站起來:“我見過的蝕魂夜,比你打理過的死老鼠尾巴還多!”
厄運小姐還沒來得及問他那到底是什么意思,就看到雷文歪過身子往她身后開了一槍。一個似乎是狼與蝙蝠混合的亡靈慘叫著消失了。她立即拔槍,打死雷文身后一個已經露出爪牙的亡靈,算是還了副官一個人情。
“大家趴下!”她大喊一聲,從皮帶上擰下兩個破片炸彈,一個高拋扔進了濃霧中。
爆炸聲震耳欲聾,木片和碎石裹挾著火光和濃煙四處飛濺。晶亮的玻璃碎片像刀子一樣瓢潑而下。廣場上只剩下辛辣嗆人的煙霧——但這里頭可沒有什么亡靈。
雷文甩甩腦袋,手指在耳朵里掏個不停。
“這炸彈是什么做的?”
“黑火藥,混上樹脂和蕓香。我特制的。”
“那些東西對亡靈有用嗎?”
“我母親相信有用。”
“夠厲害的。我覺得我們好像贏——”雷文剛要說下去。
“別說。”厄運小姐打斷了他。
霧氣再次緩緩地聚合起來。先是一束束卷須,然后現出怪獸的輪廓。拼湊起來的獸腿、含著尖牙的大口、鉤狀和螯狀的前肢……這些亡靈,他們以為已經徹底解決了。
陰云重聚,陰靈復起。
俗話說的狗屎運,到底是狗屎還是好運?
“原來死掉的人還真難殺啊。”厄運小姐強忍著恐懼,不希望別人看出來。
她太天真了,居然以為靠著一些小工具還有盲目的信仰就能跟亡靈正面較量。她原打算向比爾吉沃特的人證明,他們根本不需要普朗克。人的命運應該由自己把握。
但現在她把自己害死了不說,還把這座城市推進了煉獄。
一個低沉的號角聲掃過廣場。緊接著又是一聲。
雷聲大作,隨著風暴漸漸靠近。
不一會兒,雷聲越來越響越來越密,仿佛是一個巨人揮著鐵錘發狂地砸在鐵砧上。地面跟著顫抖起來。
“天啊,那是什么東西啊?”雷文問。
“不知道。”厄運小姐話音剛落,黑霧中出現了一個騎士的輪廓。午夜的天幕映襯著他的影子。他騎在一匹比例怪異的戰馬背上,頭盔的形狀如同惡魔的腦袋。
“是個恐懼騎士。”厄運小姐說。
雷文猛地搖頭,他的臉上已經毫無血色。
“才不是。”他絕望地說,“是戰爭之影……”
 喜歡
喜歡  頂
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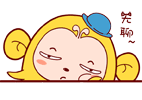 無聊
無聊 圍觀
圍觀 囧
囧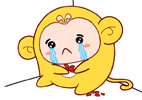 難過
難過
熱門評論
最新評論